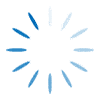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
谢枕川早有所料,从袖中取出一张泛*黄的文书来,“银作局一锤一錾皆录于册,有迹可查,还请父亲过目。”
梨瓷此刻已经彻底忘了先前的不快,也好奇地凑近去看。
信国公取来一观,的确是宫中御用的库腊笺,上面还有内廷银座局的印鉴,何时取得、何时修补、原样如何、用料多少,一一登记在册,的确合得上谢枕川所言。
信国公盯着纸笺,慢慢想起那日所见确是一支素白玉簪,后来他偷偷在嘉宁的妆奁里也遍寻不得,原以为是被藏匿到了他处,原来是另有隐情。
他此刻面皮涨得通红,哑口无言。
谢枕川悠悠道:“我和阿瓷今日拜访母亲,母亲的确提起了当年修补玉簪之事,言语中并无他意,只是埋怨了父亲多年来一根发钗也未曾送过。”
信国公沉默许久。
这话好似一把钝刀,缓缓剖开尘封往事。
先帝赐下婚约后,他亲自选了图样,花了一整年的俸禄在瑞祥楼为她打了一对赤金红宝石的镯子,去取时恰逢她出宫游玩,机缘巧合竟在瑞祥楼提前瞧见了那镯子,她当时却道:“这样粗笨的镯子,竟是瑞祥楼所制,还是赶紧收好,莫要污了本宫眼。”
他是武将出身,不通文采,更不解风情,的确不能懂她心意,更不敢再献丑。
后来见她收了周则善的玉簪,心中更是五味杂陈。
他知道自己配不上她,偏又被先帝绑在了一条船上,他能够做到的,便是最大程度地放她自由。
两人貌合神离、同床异梦,后来恕瑾长大了,她要搬回长公主府,他便也允了。
谢枕川似乎不知什么叫做见好就收,语气中暗含了几分矜诩,“阿瓷赠予我比这玉簪珍稀贵重的,不知几何,难得的是长辈心意。若要说眼皮子浅,那应当也是从未见父亲赠母亲礼物的缘故。”
梨瓷脸颊微红,小声道:“你别说出来呀。”
她又转头安慰信国公道:“父亲也不必难过,礼物不在贵重,胜在心意,您不是还为母亲摘了青梅么?”
信国公没说话,只是偏过头去,暗自叹息。
偌大一个信国公府,女儿嫁入深宫,老婆生闷气不在家,儿子是个恋爱脑,唯一一个替他说话的,居然是他从未瞧得上的儿媳。
梨瓷又道:“母亲贵为长公主,何曾缺过珠宝首饰,她想要的,不过是父亲的心意罢了。”
信国公神色微动,见梨瓷如此大度,更是心存愧疚。
他闷声道:“先前是我想岔了,误会了广成伯。今日当着……当着小瓷的面,我先赔个不是。”
他言语之间有些生硬,但的确是真心实意。
梨瓷也坦然受了这声歉意,甚至老气横秋地摆了摆手,“父亲言重了,外祖不会计较的,只要父亲母亲重归于好,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。不过母亲那边……”
她又趁热打铁,将长公主这些年受的委屈一一言明了,信国公越听越是愧疚,连将江氏母子送回祖籍之事也毫无异议。
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糊涂行径,信国公越发发起愁来,嘉宁那边如何是好呢?
梨瓷早就替他备好了,“父亲,您看这枚玉簪如何?”
信国公一听玉簪二字,便觉头大,可见梨瓷将其捧出,又眼前一亮。
眼前这枚玉簪,是极为罕见的红玉所制,玉质温润透亮,如霞光凝就,配嘉宁的雍容气度,再得宜不过了。
“好,”他厚颜收下了这枚玉簪,“放心,我不会白要你的。”
梨瓷眉眼弯弯地点了点头,也应了一声,“好。”
谢枕川又道:“父亲让母亲委屈这些年,单凭一支玉簪想要哄得母亲展颜,恐怕不够。”
信国公一看就知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,没好气道:“怎的,你还有什么馊主意?”
谢枕川侃侃而言,“古有廉将军负荆请罪,此既为家事,谢将军恐怕也要请出家法才是。”
他越说信国公越不自在,“我怎不知有什么家法?”
谢枕川一声令下,很快便有人捧着一块木砧前来,那木砧事硬木所制,上面遍布曲曲弯弯的刻痕,是捣衣所用。
信国公看向谢枕川的眼神有几分异样,“这是哪儿来的?”
“父亲不知么?”谢枕川微微一笑,不慌不忙道:“这是罚跪所用的家法。”
信国公的眼神更为一言难尽了,“你入赘以来,当真是有了不少长进。”
谢枕川神色自若道:“父亲多虑了,若无失错,自然不必受罚。”
梨瓷也在一旁点头,力争自己清白,“恕瑾哥哥没有跪过的,便是我爹爹也很少跪。”
信国公沉默了,许久才道:“为父罚你跪祠堂时,也未曾动用过这等家法罢?”
他自问不是小肚鸡肠之人,嘉宁也算大度,怎会生出这么个睚眦必报的儿子。
谢枕川面不改色道:“这是母亲的意思。”
梨瓷也替他作证,“是母亲说要负荆请罪的,恕瑾哥哥顾及父亲的面子,这才想出了折中的办法。”
信国公深吸了一口气,实在不敢想象,此事若是传扬出去,以后信国公府的脸面该往哪里搁?
谢枕川似乎看破了他心中所想,施施然道:“父亲可想好了,是面子重要,还是日子重要?”
信国公瞪了他一眼,忽然又释然了,左右自己这个儿子都已经入赘了,老子不过是罚个跪,又能怎的?
他伸手掂了掂那块木砧,咬牙道:“也罢,男子汉大丈夫,能屈能伸!”
信国公亲自提了那块木砧出门去了,一夜都未曾回府。
又过几日,两人总算和好如初,一同回了信国公府,梨瓷也收到了信国公的回礼,不过是嘉宁长公主带来的。
许是心结已解,长公主的气色都好了不少,未语先带三分笑,“先前的事,他已经同本宫解释清楚了,实在是让你和恕瑾见笑,好在都是一家人,也不怕丢脸。他还带了二十年前的那套赤金镯子来,说是要当成以后传给儿媳妇儿的传家宝,不过被本宫拦下了。”
身后的女官捧出一个木匣,长公主亲自接了过来,置于桌上。
“那对镯子…嗯…”她顿了顿,尽量找了个委婉的说法,“款式有些老气了,本宫去寻了银作局的工匠,改成了一套头面和臂钏,你看看可喜欢?”
木匣里边是一整套金丝缠枝的赤金红宝石的头面,因顾及她年纪尚小,制得精巧玲珑,华而不俗。另外那只臂钏也很漂亮,细细的金圈层叠相扣,还挂着小铃铛,有风吹过,便泠泠作响,清音悦耳。
梨瓷自是爱不释手,心中却也不免有些好奇,原先那对镯子,究竟是何等贵重,竟能打制一整副头面后,犹有余料,再添一枚臂钏?
后来还是下朝回来的谢枕川解答了她的疑问,年轻的信国公行事务求实效,与其说那是一对镯子,不如说是护臂。
-
连月来,朝堂暗潮涌动,首辅王丘亦未曾得闲。
天色还不算晚,王家府邸已是灯火通明,王丘屏退左右,独留了褚萧和、岑子民及其亲子王霁在书房议事。
王霁当年科考并未及第,是后经荫补入仕,外放历练数载,才攒足资历方调回京中,如今已擢升户部侍郎。
这几人加在一块儿,几乎已经可以成一个小朝廷了,他们今日要的议的,也自然不是小事。
王家先前费劲心机,利用褚萧和的亲事拉拢了岑子民,原以为兵权在握,起势只欠东风,如今却发觉军饷亏空甚巨。
若是以往也就罢了,偏生近日谢枕川自掏腰包为三千营补足饷银之事传遍军中,五军营与神机营闻讯哗然,将士们皆是怨声载道,沸反盈天。
与军营里的大老粗不同,在座皆是思虑繁重之人,此时再看谢枕川入赘梨家之事,便品出了几分不一样的意味来。
王丘冷嗤道:“原当他是重情之人,不想竟能隐忍至此。为了几两碎银,连入赘商贾这等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在场的人一时没说话,毕竟那可不是几两碎银。
褚萧和摩挲着茶盏,眼底晦暗不明。
他倒是早有纳了梨家那位姑娘的心思,可惜如今木已成舟,何况他的正经岳丈在此,自然也不会再提。
岑子民身为兵部尚书,对欠饷之事的弯弯绕绕最为熟悉,巴不得有人来替他平账,立刻撺掇道:“不就是钱么,谢枕川拿得出来,我等岂能落于人后?”
他的这点算盘在王丘面前自然是无处遁形,到底顾及他的颜面,王丘睨他一眼,只从鼻间哼出一声冷笑。
王霁虽然不通科举取士的策论文章,倒也有几分算才,此刻便为岑子民算了一笔账,道:“这五军营与神机营的体量,如何能与三千营作比?五军营拥兵近十万,若真要补饷银,便是一人一两,也足够我们喝一壶的。何况三千营补饷一年,你只补一月,他们如何肯依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