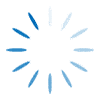她不禁轻轻晃了晃脑袋,低声感慨:“果真是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啊。”
这话没头没脑,但蓝珠却懂她意思,她走近耳房,推开窗探头望了望,附和道:“可不是嘛!安乐苑的耳房可敞亮多了,床也宽展。以前睡这儿,我夜里翻身都怕跌下去。”
楚钰芙伸手,指尖拂了拂廊下冰凉的柱子,转身向外去:“好了,咱们走吧。”
“诶。”蓝珠应声跟上。
主仆二人跨出院门,啪的一声,院门再次合拢,就好像把曾经的日子,也一并封进了木门里。
她们没有回头,步履轻快地朝着朝露阁的方向走去。
再见到白姨娘,她的小腹已微微隆起,显出一抹圆润的弧度。因着如今衣衫单薄才看得分明,等天冷了多裹几层,怕又不易察觉了。
她穿着一身嫩绿色的提花罗裙,面庞白皙透亮,眉眼间透着宁静,一眼看去,竟叫人瞧不出具体年岁。
楚钰芙随她走进内室,笑着打趣:“姨娘怀了身孕,倒比从前更显年轻漂亮了。”
白姨娘有些羞赧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,衣袖滑落,露出一对崭新的鎏金刻花镯子。
“从前太瘦了,脸颊没肉,自然显得憔悴些。如今饭□□细,也不必再熬夜做绣活贴补,每日里不过吃吃睡睡,这才几个月的光景,倒是养得胖了些。”
楚钰芙听了,忍不住好奇追问:“听姨娘这话音,近来日子是真舒心?嫡母那边竟没寻什么麻烦?”
白姨娘略一迟疑,才低声道:“我有了身孕,老爷又一直冷落她,她心里自然是不痛快。不过如今是老太太掌着家,她投鼠忌器,也不敢真有什么动作,只怕再惹出事端,老爷真动了休妻的念头。她无非是见了我,嘴巴上不饶人些,我左耳进右耳出,不往心里去便是了。”
楚钰芙点点头:“就该这样。她说什么都只当耳旁风,千万别动气伤了胎气。若真受了委屈,只管去告诉爹爹,告诉祖母,他们必定是向着你的。”
白姨娘笑了笑,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荷风苑的方向,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忧虑:“是,眼下确实还算安稳……只是,我心里总有些放不下以后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低了些:“这些日子筹备大姑娘的出阁礼,老爷对吴氏的态度,似乎略有些缓和……老爷这个人你是知道的,若大姑娘在伯府站稳了脚跟,他碍于大姑娘的颜面,也不可能一直冷落吴氏。若真让吴氏翻了身,重新拿回掌家钥匙,我怕这日子又要不好过了。”
听到这里,楚钰芙浅哼一声,端起手边的茶盏,轻轻吹开浮沫,啜饮一口,语气淡淡地:“姨娘且放宽心。吴氏若想指着嫡姐翻身,怕是打错了算盘。”
自碧虚阁开张以来,除了最初两日稍显冷清,之后几乎日日都是满客。那些夫人小姐们沐浴完毕,总爱聚在二楼歇息闲谈。
所谈之事,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。谁家公子定了哪家姑娘,谁家老爷新纳了美妾,谁家夫人气急回了娘家,哪家夫人又开罪了另一家,这小小的二楼,俨然成了京城官眷圈消息最灵通的地界之一。
楚钰芙闲时也会去二楼坐坐,总能听上不少新鲜热乎的‘秘闻’。
恰巧,她便听了这样一桩事:长平伯府的二公子任裕,看上了雾花楼一位弹琵琶的清倌人,已悄悄替人赎了身,安置在了外头,只等大婚过后接进府里。
就是前日才发生事儿。
楚锦荷素来自视甚高,倨傲得很,当初未能如愿嫁入国公府,退而求其次选了任裕,心里怕是本就有几分不甘。
任裕流连烟花之地也就罢了,若是嫁过去便发现,竟还要与风尘女子共侍一夫,以楚锦荷那性子,还不得闹个天翻?到时候她自顾尚且不暇,哪还有余力去管她娘在楚府的处境?
当然,若她是个极有城府手段的,或许能悄无声息地将此事化解,在伯爵府坐稳当。可她若是个有城府有手段的,也不会只看门第,选中这样的男人。
有些事,只看开头,几乎便能预见结尾了。
白姨娘见她如此笃定,不由好奇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楚钰无意费口舌解释这许多,只笑着安抚:“姨娘放心便是,我自有道理。”
又坐了片刻,楚铃兰得知二姐姐来了,也从西厢房过来,陪着说了会儿话。
日影渐斜,天色逐渐昏黄。丫鬟进来禀报,说二姑爷来了,正在花厅等二姑娘。楚钰芙便起身告辞,白姨娘和楚铃兰却执意要送她出门。
一行人说说笑笑到花厅找到裴越,又往大门处走,直到过了花厅,白姨娘母女才停下脚步,目送楚钰芙登上马车。
只见沉默一路的男人,在楚钰芙看不见的背后,自然而然地抬起手,虚虚护在她背后,直到她钻进车厢,才不动声色地收回手。
马车缓缓走远,楚钰芙撩起青布车帘,笑着朝院门前的二人挥手作别。
楚铃兰挽着娘亲的手臂,望着远去的马车,眼眸里露出一丝羡慕:“二姐夫对二姐姐可真好。我瞧着二姐姐最近,似乎比从前更爱笑了。”
白姨娘侧头看她,:“你二姐姐从前也爱笑呀,总是那副笑盈盈的模样。”
“不一样,”楚铃兰摇摇头,思考了一下该怎么说。
“我也说不好,就是感觉二姐姐以前的笑,笑的礼貌中带着一点客气,是习惯性的温柔。嘴巴在笑,可眼睛没在笑,总是沉沉的,盛着心事。现在却不同了,感觉二姐姐整个人轻松快活了许多,那笑意是从眼底透出来的,亮晶晶的,比以前更真,也更开心。”
白姨娘仔细回想,却分辨不出女儿说的那种“眼睛笑不笑”的区别,最终只当是小女儿家特有的敏感心思。她抬手,怜爱地摸了摸女儿脸颊。
“娘不图你将来攀上多么显赫的高门。只要对方真心待你,便是顶好的姻缘。夫君也不必非得是满腹经纶的才子,只要人品端正,能像你二姐夫这般,把你放在心里疼着护着,娘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-
京城里有一拱桥,叫作舟桥,横跨御河后半段。
过了州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街,从舟桥开始到龙津桥结束,长长一条街道烟火气十足,到处是美食摊。
楚钰芙老早就听人提起过舟桥夜市,就是总不得空来。马车穿过飘着花香的巷子,经过旌旗招展的酒楼,终于到了地方。
此刻,天色已擦黑,暮色四合,整条长街被无数灯笼点亮,橘黄色光晕连成一片。
伴着阵阵浓郁香味,中气十足的吆喝声响起。
“炒银杏、炒栗子!榆北鹅梨、樱桃煎喽——”
“煎鱼、羊脚子、热腾腾的汤骨头,统统十五文嘞——!”
“枣糕、奶黄酥、莲子杏花饮、玉冰烧酒,瞧一瞧看一看嘞!”
听到吆喝声楚钰芙忍不住撩开帘子,探头张望。
只见长街之上人来人往,一盏盏灯笼在晚风中轻轻摇曳,两侧食肆摊档的灶火熊熊,炊烟袅袅升起,飘入墨蓝色的夜空。
灯影与烟火气倒映在波光粼粼的御河水中,碎成一片流动的光斑。深吸一口气,食物的香气便盈满肺腑。
这鲜活滚烫的市井气,与元宵节那夜,是截然不同的热闹。
她扒着车窗框,转过头,一双黑眸在灯影映照下闪闪发亮:“让车夫就停在这儿吧!咱们下车慢慢逛,边走边吃,好不好?”
裴越颔首,沉声吩咐车夫停车。他率先利落地跳下马车,随即转身,稳稳地伸手扶住正探身出来的楚钰芙。
马车停下的正前方,便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羊汤摊子。
一口大铁锅架在柴火灶上,奶白浓郁的羊肉汤在里面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,升腾起大片白蒙蒙的热气。浓郁的羊鲜味混合着辛辣的胡椒香气,直冲鼻子,勾得人流口水。
楚钰芙刚在青石板路上站稳,反手便扣住了裴越的手掌,拉着他兴致勃勃地朝那摊位走去,扬声问道:“店家,羊汤怎么卖?”
摊主是个手脚麻利的中年汉子,闻言抄起大勺,舀起一勺滚烫的汤汁,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白亮的弧线,嗓门洪亮:“客官里边请嘞!清汤十三文一碗,带肉的二十文一碗!用的都是今早现宰的新鲜羔羊,保准儿香!”
“来一碗带肉的!”楚钰芙笑着应道。
裴越剑眉微挑,看她一眼:“一碗?”
楚钰芙拉着他挤到一张简陋的小板凳上坐下,解释道:“一碗就够啦!咱们俩分着喝。你瞧瞧这条街,望都望不到头,得有多少好吃的等着咱们?要是刚来第一家就吃饱了肚子,那怎么行?”
说完,她目光落在男人淡色的薄唇上,狐疑道,“……夫君该不会是嫌弃我,不愿和我同吃一碗吧?”
成婚数月,更亲密的事情都不知做过多少回了,口水也早不知交换过多少,难道还介意同吃一碗汤?
裴越被她这小眼神看得啼笑皆非。
相处日久,他越发看清自家这位小夫人的“真面目”。在外人面前,她是端庄温婉、举止得体的贵女;在自己面前,则多了分小性子,爱吃亦爱躲懒,脑子里还时不时冒出些古灵精怪的念头。
他唇角几不可察地微微勾起,带着一丝纵容:“自然不嫌弃。就依夫人的。”
小小的羊汤摊坐满了食客,人声嘈杂。
他们旁边的矮桌上坐着一对年轻的小夫妻。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麻布短打,像是店铺伙计。女人一身朴素的粗布裙,两人只要了一碗带肉的羊汤,各自捧着一块烤得焦黄的油饼,头挨着头,边小口吃着饼,边低声说着话,脸上漾着笑意。
看着他们,楚钰芙恍惚间想起了自己大学时的事。
那时她为了赚生活费,在校门口的麻辣香锅店里兼职做服务员,那家店味道好量大,学生们常来。她总能看到一些小情侣,点上一份麻辣香锅,头碰头地挤在一起,你喂我一口,我夹你一筷,说说笑笑,黏黏糊糊。
她倒并非羡慕,只是这相似的场景,勾起了些许遥远的记忆。
裴越见她目光怔怔地落在那对夫妻手中的油饼上,以为她也想吃,便径直起身走到摊前,买了一块烤得酥脆喷香的油饼,塞进她手里。
恰在此时,摊主端着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汤过来了,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。
楚钰芙看看手里温热的油饼,又低头看看面前奶白汤面上的翠绿葱花,不自觉地往裴越身边挪了挪凳子。
她咬了一口酥脆掉渣的油饼,满足地眯了眯眼,然后凑近裴越,小声笑道:“夫君,你看我们现在这样,像不像一对最最寻常的小夫妻?”
裴越微微侧头,暖黄的灯笼下,看见她白嫩的脸颊上沾了一点碎饼渣,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指,动作轻柔地为她拂去。他低沉的嗓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:“我们本就是寻常夫妻。”
楚钰芙舀起一勺滚烫羊汤,小心翼翼地吹了吹,舒舒服服地喝下去,暖意瞬间从喉咙蔓延到四肢百骸。她惬意地晃了晃脑袋,带着点促狭的口吻打趣道:“寻常夫妻可不会动辄纳妾。”
这个时代,但凡有些权势钱财的男子,哪个不是三妻四妾?她爹楚老爷有两房姨娘,信国公府也有一位春姨娘,就连裴尚书,听说早年也有通房。
她话音刚落,便听见身旁男人那低沉嗓音响起:
“不会有妾。”
嗯?什么?
楚钰芙一时没反应过来,手中的勺子顿在半空。她愣了两秒,才有些茫然地抬起头,直直撞入男人那双深邃专注的桃花眼中。
只见他眼帘微垂,眸光沉静而认真,一字一顿,清晰地重复道:“有你足矣,何须纳妾。”
楚钰芙只觉得周遭鼎沸的人声、摊贩的吆喝、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瞬间都如潮水般退去,世界陷入寂静。唯有自己胸腔里那颗心脏,正在疯狂地、毫无章法地擂动,咚咚咚的巨响几乎要震破耳膜。
一股热意倏地从脖颈蹿上脸颊。
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些许手忙脚乱,慌忙低下头,掩饰性地清了清嗓子,拿起勺子无意识地搅搅碗中汤水,试图岔开话题:
“啊,对了!差点忘了件正事要同你说……嗯,我爹今日找我了,说工部的胡侍郎因病告退了,眼下这位置,便空出来了。”
第80章
裴越脸色丝毫未变,就着楚钰芙的手,低头在那块酥脆的油饼上咬了一口,慢条斯理地嚼着咽下,才抬眼问道:“岳父让你来探探口风?”
楚钰芙点头:“嗯。”
“那你怎么想?”裴越的目光落在她脸上,带着询问。
楚钰芙抬起头,视线越过喧嚣的食摊,投向夜市里摩肩接踵、为生计奔波的寻常百姓。一片树叶从天而降,悠悠飘落在石板路上,于她眸中划出一抹秋凉。
“我父亲这个人啊,”她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“薄情、自私,一心只装着自己的面子与官声仕途,这些,重过一切。”
“我虽不大懂得工部侍郎具体掌管些什么,却也明白一个道理,官位越高,肩上担的责任便越重。我想请你同裴伯父*讲一声,不必顾虑我,更不必因我的缘故有所偏向。举荐真正有才干、堪当此任之人,方是正理。”
于私心而论,因着万姨娘那桩旧事,她便不愿看到楚老爷再攀上一步。
若说吴氏失去管家之权,失去光鲜亮丽的虚荣生活会让她生不如死,那么对楚老爷而言,还有什么比毁掉他汲汲营营、心心念念的晋升之路更令他痛彻心扉?
人总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