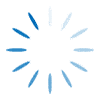该如何忘记?
剜心剔骨,剥皮抽筋,还是寄希望于神话故事中,莱忒河的水?
她想要忘记他。
不仅是他。还有那个在他怀里哭、笑、赌气、活得彻底的自己。
所以,要忘掉他,就意味着她要否认整段人生。
那不只是心脏剜去,那是要连同时间一起焚毁。
而人是无法和自己的时间和解的。
这是爱吗?
如果“爱”意味着温柔、理解、互相成全,那这绝对不是爱。
可如果“爱”是一个人明明知道会毁灭,还是一头撞上去,还在残骸里一遍遍摸索那点熟悉的温度,那这就是爱。
它像一棵被风折断的树。
根还在地下,树干已经干裂,它不是活着,也不是死了。
它只是在那儿。
那不是爱留下的印记,是存在留下的痕。
时间流淌过她的身体,那是一条看不见的河,从心口淌下去,流过她的胸腔、手腕、指尖,每一息的脉搏,也就是河流的潺潺。
那里有一个人的名字。
爱愿生啖其肉。
恨至结草衔环。
简随安以为,死亡,是答案,能让她忘记他。
可她数完那一粒粒药片,放在掌心的时候,她又想起他了。
没有逻辑,没有因果,只是下意识的想起。
她的身体在记得他。
她的记忆比她还忠诚。
想起他的声音。
那声“安安”。
低低的,带着笑意,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像落在她的颈侧,带着呼吸的温度。
她忽然想,他现在在做什么,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喝茶、看文件,眉头微微皱起。
他从不慌乱,从不失态。
连她哭的时候,他都能从容。
所以,她太想忘记他了……
刺眼的白。
她的喉咙发干,嘴里有苦味,胸腔里像塞着一团湿棉花。她试着动一动,连睫毛都沉得厉害。
然后,她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。
很淡的烟味,混着冷茶和一点檀香的味道。
她还没睁眼,就知道是谁。
她不想睁开。
可意识已经往上浮,像被一只手强行拽出水面。她终于把眼睛撑开一道缝。
他坐在床边。
她的嘴角动了一下,不知道是想笑,还是想叹气。
还是他。
连死都没能离开。
她忽然觉得累。
那种累,不是身体的,是命运的,一点点消磨了她的骨血。
她闭上眼。
隔了几秒,才轻轻开口。
“我想去澳洲。”
她不想看他。
也没有解释。
仿佛那不是请求。
而是唯一剩下的出口。
他答应了。
医院消毒水味太重,像是冷水泡开的铁锈,混着酒精和一点点甜腻的粉末气。一呼吸,整个人都被那股干净得过头的味道灌满。
像在提醒她,这里不属于生命,只属于抢救回来的人。
她想离开。
他点头,说:“好,我们回家。”
家?
简随安看着他。
她哪里还有家?哪里是她的家?是他给她的那间屋子?
那不是家,那是她被收藏的地方。
可她还能去哪儿呢?
她想死,没死成,是天不收她。
她父母不爱,命薄缘悭,人不怜她。
她自堕迷津,阴司泉下,怕是连鬼都嫌她孽重。
唯有的那么一点恩情,被她握住,当成救命稻草,也把自己赔了进去。
她早已无处可去。
夜深以后,整栋房子安静得过分。
她躺在床上,睁着眼。客房的天花板有一条很细的裂纹,她盯着那条线,看了很久。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门没有关严,留着一道缝。
她不知道是自己留的,还是他故意没有关紧。
那道缝里透出一点走廊的光。再远一点,是书房门下的一道灯影。
他在。
她知道他在。
半夜,她真的醒了一次。
不是噩梦惊醒,是突然心脏一紧,像是失重。她坐起来,呼吸有点急。下意识看向门口。
灯还亮着。
她怔了一下。
几分钟后,书房那边传来一点动静。
脚步声很轻。
可简随安看见了光影的晃动。
她知道他停在了门外,但没有推门,只停了一瞬。
然后,他回去。
夜晚,他们之间隔着一条走廊。
不远,却像两岸。
白天更难。
夜里还能假装,假装是看护、是照顾、是她需要休养。
可白天,光线是诚实的。
窗帘半掩着,光从缝里斜斜照进来,在地毯上拖出一块温热的影。
简随安坐在沙发上,膝上摊着一本书,却一页都没翻。
宋仲行在不远处,看文件,笔尖偶有落下的声音。
风吹过,窗帘轻轻掀动。那一瞬,尘埃在光里翻滚。
屋子静得过分。
像一座墓。
埋着他们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。
简随安每天都醒得很早。
但不起床。
窗帘拉着一半,光从缝里斜进来,落在地板上。
她躺着,看着那条光一点点挪。
他已经起了。
在书房,开电脑,打电话,声音都压得很低。
出门前,他会在门口穿好外套,回头看她。
她坐在餐桌那边,目光却没什么焦点。
她从不问他去哪儿,从不送他出门。
像一个礼貌而冷淡客人,又或者,是真的没了力气。
白天会有医生上门复查,她下午还要按时出门散步,每天的生活平静而又规律。她也在等,等出国的手续办下来。
她还要待一个月。
她需要休息。
那天下午,她突然走进书房。
“你在忙吗?”
他抬头,看她一眼。
“没有。”
然后她就坐下。
不说话。
只是在他旁边待着。
她看见那个杯子了。
她亲手做的。
陶瓷的,杯口处的淡蓝色花纹,杯身的最底下刻着日期。
她还记得。
在大叁,下午,宋仲行在客厅的桌子那边,她一个人抱着一本厚厚书,翻来覆去地查。
她叹气:“你知道吗?我们的属相不合。”
他当时抬眼看她,笑了一下。
“哦?那怎么办?”
她认真得不得了,仿佛是什么天大的事。
“要不你把你的八字给我,我再看看,听说有人八字特别合,就是属相不合。”
她本来是不信这些的。
可她需要一点证明与安慰。
她想在所谓的天命那里,找到一点站得住脚的理由。
她想选一个黄道吉日,要一个看似有天意站队的安全感。
她问:“要不要找个师傅看看?”
他轻轻笑一声,摸了摸她的脑袋。
“你要是觉得安心,我们就看个日子。”
那是个很好的日子。
那是黄历上写着的“宜嫁娶,宜祭祀,宜纳采”的日子。
甚至连名字都吉利得过分。
那日子很快就到了,就在明天。
简随安在书房,愣愣地发着呆。
夜里,北京的风刮过窗沿,带着一点未散的寒气,秋末了。
凌晨一点。
屋里忽然传来一声极轻的动静。
一道急促的抽气,又骤然没了力气
他站了起来。
走廊很长。灯没开,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月光,冷白一片。
他先是停在她门外,没有立刻推门。
里面传来极低的一声哽咽,压着的,像是怕吵到谁。
他推门进去。
屋里只开着一盏床头小灯。她侧躺着,额头全是汗,头发贴在脸上,呼吸急促,像刚从水里捞上来。
她醒着。
但没有完全清醒。
目光茫然,意识是散开的。
他走近一步。
她忽然开口,很小声的一句:“别关门……”
语气轻飘飘的。
他站在床边,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坐下。
床垫轻微下陷。
她的肩膀立刻绷了一下。
他伸手,指尖靠近,是先替她把汗湿的头发拨开。动作很慢,指腹碰到她太阳穴的时候,他停了一瞬。
她回过神,看到是他。
没有惊讶,也没有排斥。
是那种疲惫的、快要散掉的神情,忽然有了着落。
她往旁边挪了一点,空出位置。
他没有说话。
脱掉外套,放在椅子上,然后躺下。
中间留了一点距离。
谁也没有主动靠近。
可没过多久,她的手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。
轻轻地,碰到了他的手腕。
像确认温度。
他没有抽开。
过了一会儿,她整个人往他这边靠了一点。额头抵在他肩上,呼吸渐渐慢下来。
他这才伸手。
没有紧抱,只是环过去,让她有地方依靠。
那动作不似从前的亲密。
太小心。
她睡着了,呼吸变得均匀。
他却没有。
两个人重新躺在一张床上,同衾共枕。
他会在夜里忽然睁眼,确认她还在怀里,确认她没有悄悄抽身。
有时候她翻身,他会下意识伸手去抓她的手腕。
抓住了才放松。
那是恐惧。
他不说。
他永远不说。
可身体是诚实的。
她也是
她感到安心。
这是一种病态的习惯,也是残存的爱意,是两具彼此撕扯的灵魂,在对方的温度里勉强苟活。
第二天,家里来了几位外人。
文件一页一页摊开在桌上,纸的边缘反着光,笔从她手里递过去。
她要填写的材料很多,桌上那堆文件足有一厘米厚。有英文字母,也有汉字,有打印的格线,也有手写的批注。
她眼睛一行行扫过去,却什么都没看进去。
每个字都像糊开了。
她太累了,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不成样,一笔一画写完,她交过去,起身就离开了。
而很快,她就能彻底离开了。
她不想再回来了。
她想忘记他。
忘记那张熟悉的脸,忘记他的气息、他的声音、忘记他唤她“安安”时,那种温柔到会让人沉溺的错觉。
可她还不知道。
忘记并不能让她自由,记得也不能让她幸福。
他们之间的安静太浓稠,像一场漫长的呼吸,一旦靠近,就会烧起来。
她闭着眼,贴着他的胸膛,所有的声音都慢了。
空气里是皮肤的热,以及某种被困住的安静。
身体知道在靠近。
可心却在后退。
思绪在黑暗里乱成碎片,她看不清自己的边界。
有一瞬,她听见血在身体里走路,一声一声,撞在骨头上。
那声音在问她:这是爱吗?
她想说不是。
又说不出口。
他在她耳边低语,呼吸扫过皮肤的地方都发烫。
“安安……”
他在喊她。
是一种带着回忆、心疼、哀怜与占有的声音。
像是在召回一只受伤的雏鸟。
那声音轻得几乎要碎,尾音压低,带一点气息在喉咙里转。
简随安有些恍然,她发现,好像只有他会喊她“安安”。
她开始回忆,她想知道,他第一次这样喊,是在什么时候。
也许是在很久很久以前,一个几乎被时间磨得模糊的午后。
那天阳光有些晃,书房的窗半开着,空气里有股槐花香。
她刚写完作业,铅笔一掉,滚到了桌子底下。她正要钻进去捡,却听见他的声音从书桌那头传来。
“安安。”
他第一次这样喊。
声音不高,不急,也不重。
那时候她还小,不懂为什么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只记得那一刻,她忽然不敢抬头。
像是鸿蒙初开,天地混沌,她从无到有,被他那一声“安安”唤醒。
她的名字就是他的声音。
从那以后,她就再没能忘掉。
简随安的眼泪落了下来。
芒种有叁候。
一候螳螂生。
深秋埋下的卵,在初夏破壳而出。
那像她。
她以为自己是在夏天爱上他的,在那种喧闹的,吵闹的,最热烈的时节。
可其实不是。
那颗心早在更早、更冷的时节里埋下去了。
等到阳光炽烈,她不过是破壳。
二候鵙始鸣。
伯劳鸟叫得很急,很清,很锋利。
像是生怕谁听不见。
她后来一点点地失了分寸。
哭、笑、撒娇、赌气、挑衅、嫉妒。
她用声音、用身体、用全部的存在感提醒他——她在。
她要他。
她那样热烈,像伯劳鸟一样,拼命鸣叫。
叁候反舌无声。
百舌鸟停了。
天地忽然安静下来。
芒种之后,便是夏天最盛的时候。
万物生长,也万物耗尽。
世间所有盛夏,终要归于寂静。
她以为那就是结束,是终点,是落幕。
可他喊她的名字。
“安安……”
像一根线,把她从梦、从恨、从远方拉回来。
耳鬓厮磨,几乎贴着她的唇。
又似乎不是在叫她。
只是想确认她还在。
他一遍遍地喊……
而也正是这一刻,所有“想忘记”的念头都化成了回声。
越是想远离,他的声音就越在心里回荡。
一遍一遍撞在她胸腔里,都已经织进了她的骨血。
她想忘。
可她一动念,那念头本身,就是在记得。
她会想到什么?
想到六岁那年,他会抱着她,接她放学,听她叽叽喳喳地说起学校的事情。
想到初一那年,是他在她的作业本上签字。
想起他每次出差回来,总会给她带那边的特产,又或者是一点稀奇的小玩意。
想到她在院子里追猫,他在阳台上看,一边看让她“慢点跑”,一边轻声笑。
想到她在他的怀里,他在她耳边呢喃的名字。
那两个字,是她的原点。
简随安笑了出来,泪从眼眶溢出来,滑过她的眼尾。
他俯身去吻。
他的指尖沿着她的肩、臂、腰蜿蜒过去,每一下都像在描记。
她没有避。
反而抬起手,捧着他的脸,她的鼻尖擦过他的下颌,带着一点潮湿的热气。
她的唇轻轻贴上去。
一遍遍的,她像是要把所有未说出口的痛意、所有想忘的念头,都埋进这个吻里。
他的温度,他的气息,他多年来笼罩着她的影子,还有,他喊她的名字。
“安安。”
名字,像是灵魂的形状。
能被看见,能被碰触,能被记得。
而一个人第一次喊另一个人的名字,便等同于在时间的浩流中替她开天辟地。
她的呼吸一点点乱掉,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上来,把他的脸映得模糊。
可她还是能看见他的眼睛。
看见他瞳孔里映着自己的影子。
那是她存在的证明。
她的眼泪在他们之间糊成一片温热的雾,顺着他的嘴角、下巴,一滴滴落下去。
她终于轻声开口,看着他。
“我想记得你啊……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