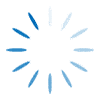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
谢枕川从公务里抬起头来,“困了?”
梨瓷已经顺势趴在了桌案上,枕着自己的手臂点了点头。
“我抱你去里间睡。”
谢枕川将她打横抱起,慢慢步去里间,此处设了一张美人榻,他偶尔会在此小憩。
一躺下,梨瓷反而不那么困了,她伸手拉了拉谢枕川的衣袖,还惦记着方才未看完的话本,“我的书。”
谢枕川就着她的力道附身下来,却只是亲了亲她的额头,“起来再看,仔细看坏了眼睛。”
他的声音极尽温柔,梨瓷松了手,听话地抱着薄毯点头。
窗外鱼池的水汽混着荷风潜入,她蜷在薄毯里,数屏风上的花鸟纹,外间不时传来轻缓的书页翻动声,慢慢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
知道世子夫人在里间休憩,南玄蹑手蹑脚地过来禀报,“世子,国公爷来了。”
谢枕川颔首以示知晓,随手捡了封文书,盖住了那本格格不入的《花灯轿》。
信国公正好推门而入,他顺势起身行礼道:“父亲。”
案前圈椅铺着云锦软垫,比硬邦邦的木头舒适,一看便是给自己留的。
见儿子有心,信国公态度也软和了些,亲自拉开椅子坐下,“今日朝中如何?”
谢枕川原不想在此处议事,侧眸望了一眼屏风,并未见什么动静,这才低声道:“王丘的动作很快,不过月余,朝中官员已有多处更替,今日还有人廷谏圣上早日立储。”
王、谢两家皆知,这几年奏请皇帝立储的折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,皆是留中不发,但在谢枕川还朝当日便提起此事,可谓是“用心良苦”了。
信国公眉头紧锁,“应天帝怎么说?”
谢枕川轻描淡写道:“罚俸一月。”
不过是王家推出来的跳梁小丑,他连此人的名字都未提。
众人皆知应天帝有意推延此事,还敢在上朝时当面提及,打的何止是谢家的脸,亦是应天帝的脸面。
信国公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,毕竟二皇子年岁太小了,拖延下去,对自家反而有利。
有些话在西厅里不便多说,他回去左思右想,仍觉不妥,这才来了谢枕川的书房。
“你方才问及三大营军饷,可是其中有什么隐情?”
谢枕川颔首道:“今年国库亏空,南边治水又要不少银钱,户部、兵部和工部在朝会上起了不小的争执,三大营的军饷恐怕是要拖些时日了。”
信国公沉吟片刻,“治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可将士们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,若是一两月也就罢了,经年累月地拖欠下去,不是好事,何况你新官上任,若连军饷都不能保足,如何立威?”
谢枕川拿出一本账册来,用轻飘飘的语气说着足以撼动朝堂的大事,“这几年国库虽然空虚,好在边关还算安定,已经有人动了主意了。我查过账册,三千营的军饷本就未曾足额发放,若是再有将领克扣盘剥……”
他言已尽,却意味深长。
信国公看不懂账册,但他也知晓军营里折色抵饷的手段,面色越发凝重了,忍不住问道,“既然问了先前,如今三千营每月饷银多少?”
谢枕川比出一个的手势,“不到五钱。”
“怎会如此?”信国公气得要拍桌,却被谢枕川拦下了。
他以为谢枕川是担心自己弄坏了账册,便收了手,憋着火道:“那另外两营呢?”
“已经派人去查探了,”谢枕川顺手收起信国公面前的书册,不动声色道:“看今日朝上岑大人幸灾乐祸的样子,应当比三千营好不少。”
见他提及昔日好友,信国公不由得叹了一口气,“也罢,先去军营里走一趟吧,可要我随你一道去?”
他虽然解了兵权,到底还有几分薄面。
谢枕川摇了摇头,“父亲不必担心,孩儿已有打算。”
见他这样说,信国公也不勉强,点点头,暂且离去。
待脚步声远了,谢枕川便去了里间,原是要替梨瓷掖被子,凑近了些,才发现她并未睡着,此刻眨巴眨巴眼睛看着自己。
谢枕川在榻边坐下,轻轻揉了揉她头上的穴位,“吵醒你了?”
他指上力道恰到好处,梨瓷颇为不舍地摇了摇头,坐起来关心道:“恕瑾哥哥要出门吗,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?”
谢枕川弯了弯唇角,宽她的心,“小事罢了,阿瓷不必挂心。”
梨瓷紧紧抿着唇,前思后想,“可若是不给底下的人发工钱,谁还会听你的呢?”
难得见她这般认真模样,谢枕川伸出手指,抚平她蹙起的眉心,“无妨,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若是别的事,梨瓷的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,可若是和银钱有关,那便不一样了。
“爹爹说了,能够用银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,”她握住他的手指,慷慨道:“差多少钱呀,若是差得不多,先用那笔聘礼将亏空补上?”
谢枕川微微一怔,想起梨瓷先前倾其所有给出的聘礼,眼中浮起一丝笑意来。
他将梨瓷拥入怀中,下颌轻轻抵在她发顶,“虽是阿瓷给的聘礼,但既然已经入赘了梨家,便还是阿瓷的,哪有用你的银子补贴官家的道理?”
他很有赘婿的自觉,也并不打算用这笔钱。
“至于军营那边,屯田或是弄些盐引、茶引来,也可弥补些许亏空。”
清冽的茶香袭来,比方才的柿叶茶更为诱人。
梨瓷立刻生出千金买笑的豪迈来,一心护着自家的赘婿,“反正银子放着也是放着,不如替你省些时间,日后再慢慢屯田,将聘礼赚回来。”
谢枕川没说话,梨瓷靠在他心口,忽然“呀”了一声,转过头,一脸无辜地看着他,“恕瑾哥哥,你心跳得好快。”
-
京郊,三千营驻地。
时值初夏,本该是操练最勤的时节,可校场上却空了大半,仅有的几个士兵也提不起精神,歪歪斜斜地拄着长枪,活像是晒得焉头焉脑的狗尾巴草;有人蹲在墙角斗蛐蛐,赌注是明日早饭里唯一的一个鸡子;更多得是人枕着锈迹斑斑的盔甲打盹,鼾声混着蝉鸣,在浮躁的午后格外刺耳。
副将郭调途经此地,也赌了一个鸡子,眼看他押注的那只蛐蛐就要落败,他忽地站起身来,“哐当”掀翻了那只充作斗栅的豁口陶碗,一本正经道:“干嘛呢,都什么时候了还斗蛐蛐?不知道新任提督要来?我看你们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!”
“哎呀!”
有的人惊呼,有的人惋惜,到底还是起身慌忙走了几步,却又在几步外重新聚拢。
蛐蛐儿斗不成了,几人又闲话起来。
“三大营换将,又不止咱们三千营,也没见怎么着。”
“我怎么听说五军营那边新任的提督是户部尚书的侄子的连襟,关系铁得很,他们马上就要补发一半的饷银了。”
“放屁!我表兄就在五军营当差,也就比我们强一点罢了,能把先前那一半发下来就不错了。”
“那也是比我们强啊,每个月就这么三瓜俩枣的,还不如去当个护院呢。”
……
郭调听得无奈,但拖欠军饷也是事实,他原先还管,现在便也由得他们去了。
他拍了拍衣袖上的尘土,嘱咐道:“谢提督今日要来军营,你们留点神,别老是这般不着四六。”
兵卒们含混应了一声,又蹲进草丛里找方才那两只蛐蛐去了。
-
马车辘辘驶向京郊三千营驻地,畅通无阻地进了提督营房。
三千营这般死气沉沉的样子,谢枕川在来时路上便已经领教过了,他无意追究,只是让人将副将郭调叫了过来。
郭调行了礼,罩甲跟着他的动作哗啦作响,“下官郭调,拜见谢大人。”
他没忍住偷偷抬眼,这位新任提督生得一副好皮囊,玉冠长衫衬得人如修竹,实在是……一副小白脸的长相。
谢枕川也扫了一眼他的罩甲,一看便有些年头了,上边有好几处甲片掉了,也没有补。
他开门见山道:“今日朝中议事,三大营军饷要延后发放的消息,你们可曾知晓了?”
郭调忍住翻白眼的冲动,点了点头。
谢枕川又道:“三千营历年欠饷几何,你算个总数。”
“下官是副将,不是账房。”
濯影司指挥使的大名在权贵之间自然如雷贯耳,可在这群兵油子里边,就没那么好使了。得知他舍弃男子颜面入赘,如今入营也是携眷而来,郭调便更看不起这个小白脸了。
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,又咧嘴一笑,“算出来又如何,难道谢大人要替我们补?”
只是话一出口,他就后悔了。
他久经沙场,感官比常人敏锐不少,谢枕川虽然神色如常,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眸却倏地冷了下来。
谢枕川仍是不紧不慢道:“确有此意。”
虽然气势已经矮了,郭调心中仍然不信:如今国库亏空,五军营与神机营由大皇子的人接手,背靠内阁,都填不上窟窿,他不过一个濯影司指挥使,哪里来的银子?